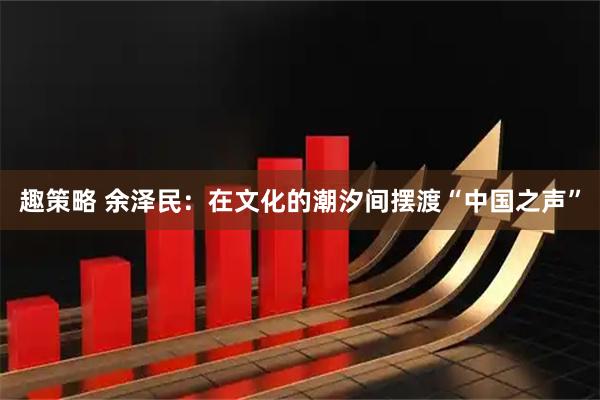

余泽民趣策略
翻译家,作家,现居匈牙利布达佩斯。翻译凯尔泰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艾斯特哈兹、马洛伊、纳道什等匈牙利重要作家的作品二十多部,被誉为“当代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曾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中山文学奖”“开卷好书奖(翻译类)”和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
从漂泊的异乡人到匈牙利文学的“中国之声”,从医学毕业生到著名翻译家、作家,余泽民的故事由无数偶然与必然交织。他与诺奖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以下简称“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友谊,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文学圣殿的大门。如今,余泽民在中国教授文学翻译,定居在匈牙利专注翻译,甚至互译,两个不同国家的生活却有着共同的目标——挖掘优秀的文学作品,促进中匈文化交流。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创作,把自己脑子里构想的故事写下来。在文化苦海的潮汐之间,余泽民以语言为桨,甘之如饴。
处于低谷的“莲花”
遇见李白“狂热粉”
跟余泽民的聊天话题依然从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开启。他特意嘱咐,“文章一开始要写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全名,匈牙利人姓在先名在后,即使简化也要用‘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尽管这个家姓有点长,但这是对他的尊重,只有熟人才能直呼他‘拉斯洛’,好朋友则用昵称‘拉茨’。”
随着诺奖话题热度的攀升,余泽民应邀在很多公开场合谈论这位作家挚友——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我跟拉斯洛的故事挺有趣的。初遇时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却把他给‘迷住’了。他说,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意思是第一个可以敞心交谈的中国人,而他是一个‘中国迷’。”
时间回到1991年年底,余泽民孤身乘火车抵达匈牙利。在一个叫塞格德的南方边城,他寄宿在好友亚诺什家,“亚诺什当时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学(现塞格德大学)任教,创办了一份影响很大的文史杂志,不仅是出版人,还是当地的文化名人。那时我正处于生活的最低谷,由于签证问题成为了‘黑户’,并且失业,疲于谋生。某社交平台网传的那些经历,例如,诊所医生、家庭教师、插图画师、导游、翻译、编辑、记者,并不夸张,甚至剥蒜、摘果,教做中餐和简化太极,这都是我尝试过的谋生之路。当时的我,与其说寄宿他家,不如说是被他收留。”
1993年4月初的一晚,在亚诺什家常办的文化沙龙上,来了一位被称作“未来最优秀的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高个子,高额头,长发齐颈,戴一顶卡夫卡式的黑色礼帽,略微驼背”是余泽民对他的第一印象。尚未熟络,这位客人就开始了“疯狂输出”,缠着余泽民聊起他能聊的关于中国的一切。
当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已凭处女作《撒旦探戈》成名,而且在1991年首赴中国,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但由于是官方邀请,官方安排,让他觉得“隔着一层玻璃”看中国,没有机会与当地人自由交流。“但是即便这样,还是很美好,从中国回来,他向家人宣布用筷子吃饭,而且不管去哪儿,都注意搜集关于中国的一切,尤其是古代中国。他喜欢诗仙李白。我当时还不会匈语,好在我可以跟拉斯洛用英语交流。”
聊到兴奋之处,作家让余泽民朗诵一首李白的《赠汪伦》,“我还用毛笔抄写下一首《早发白帝城》送给了他。我们聊得投机,他索性连夜驱车邀请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
余泽民记得,他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才到达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住处,那是距离布达佩斯三十多公里的一座山乡。彼时天蒙蒙亮,雾气正浓,映入眼帘的是一所盖在果园中的石头房子,屋中的书架直抵天花板,像极了一座世外图书馆。之后的几天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会热情地将余泽民介绍给周围的每个人,“他总说,我是他最好的中国朋友,其实,他只有我这一个中国朋友。”余泽民笑道。
“拉斯洛的写作特别有规律,早睡早起,通常凌晨起来写到天亮。白天要么出去见各种朋友,或在家里接待客人,他不管去哪儿都把我带在身边,在家的时候,我会给他做中餐。”在拉斯洛家,余泽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除了很多画册之外,还读了当时对他来说都属于“知识盲区”的《道德经》《周易》。“要知道,我是六十年代生人,对国学的了解并不多,八十年代疯狂读书,但读的更多是世界名著。倒是在拉斯洛家读了很多关于古代中国的书。”
从那之后趣策略,余泽民走进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生活。后来,余泽民偶然从亚诺什口中听到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对他的比喻,“他说我是一朵莲花,可能我说话少,符合这种东方人的含蓄。”这个比喻被赋予了美好的东方意象美,“我一辈子没听过有人这么夸我。”余泽民回想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就在那次,两个人有了一个约定,就是有一天余泽民要陪拉斯洛去一趟中国。后来,五年后这个约定真的实现了。正是1998年的那次中国之行,将余泽民引上了文学之路。
冥冥注定的文学路
1999年,余泽民翻译了他的“处女译”,那是拉斯洛的一个小说《茹兹的陷阱》,那个短篇收录在名为《仁慈的关系》的集子里。“我之所以会对拉斯洛的作品感兴趣,是因为1998年5月陪他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一个月的中国之行,我们一起走了大概十座古城,一路上进行了大量采访,话题就是围绕‘李白’。回到布达佩斯后,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整理了十四盘录音磁带,这次旅程促成拉斯洛写了一篇游记《只是星空》。正是那一个月的深度接触,让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说来也巧,亚诺什正好再版了他的短篇小说《仁慈的关系》并给了我一本,我选了其中一篇相对难度较小的小说开始翻着字典翻译起来。”
《茹兹的陷阱》译成中文还不到一万字,却花费了余泽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也正因如此,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我被如此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吸引住了,这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越难越想读,还染上了‘翻译瘾’。”不到三年时间,余泽民翻译了二十多位作家的三十多个短篇小说。沉醉于翻译世界的余泽民,当时还并不知道这是即将开花的机会的种子。“我从没想过这些译稿能够发表,对我来说,这些翻译只是为了自学匈文和文学阅读。”
时间来到2002年,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国内几家出版社争夺图书的出版权。经过一串戏剧性的故事,余泽民不仅为作家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找到了凯尔泰斯的外文版权,还借助于那30多篇译稿,取得了朱燕的肯定和信任,签下《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船夫日记》这四本书的翻译工作。“当时,我意识到这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机会,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我几乎没有脱衣服睡过觉,甚至不舍得花时间洗澡,困了就在键盘上趴一会儿,拼命翻译完了四本书,并且翻译质量得到了承认。”事实上,凯尔泰斯的作品对余泽民来说翻译难度很大,不仅题材陌生,而且极富哲学性,但他凭着勤奋和过去知识的积累顺利完成了翻译任务。
对余泽民来说,正是这次翻译工作将他正式引上了文学翻译之路。从2006年1月开始,经周晓枫的介绍,上海的双月刊《小说界》主编魏心宏老师委托余泽民开设一个名为“外国新小说家”的专栏,从那之后的十年里,余泽民在这个栏目里翻译介绍了六七十位作家的作品,而且都是当时国内还不熟悉的新面孔。当然,余泽民第一个就推荐了拉斯洛,不仅刊登了那篇《茹兹的陷阱》,还写了一篇《拉斯洛的中国情结》。之后,他还推荐诸如伊恩·麦克尤恩(获布克奖、费米娜外国小说奖等国际奖项)、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波兰小说家、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等作家。2015年,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得了国际布克奖,人们才注意到余泽民的“先知先觉”。一年后,余泽民翻译了《撒旦探戈》,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正式与中国读者见面,之后他还翻译了拉斯洛的《反抗的忧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等。“回想初相识的场景,我们俩都不曾想到,我会成为他的中国声音。”
就在余泽民翻译期间,他还感受到了创作的乐趣。“出国之后,我虽然一直有记录日常的习惯,但从没有尝试过写小说。但经过大量的翻译练习,我对创作产生了兴趣和冲动,因为创作让我更自由,手握主动权,能够操纵人物命运,创造全新的世界。于是,我也开始尝试着写东西。2000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匈牙利舞曲》完成了,之后的三年里,陆续写了十几篇作品,但也并没有想过能够发表。”2005年,又是一串戏剧性的故事,在白描老师的赏识下,他的十几篇小说先后在《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大家》等一线文学杂志上发表,同年结集并被选入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与徐则臣、张楚、王棵等同时出道。
在余泽民的文字中融合着生活经验与细腻情感,成就了重要的匈牙利三部曲——《匈牙利舞曲》(2005年,作家出版社)、《狭窄的天光》(200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纸鱼缸》(2016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其中,《纸鱼缸》在20世纪中国与匈牙利宏大历史的背景下,展现了青春舞台的易逝性和现代人的孤独生存状态,采用交错叙事结合隐喻、意识流等手法,被评价为“对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和凯尔泰斯的文学致敬”。此外,余泽民还发表了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等作品。
余泽民说,翻译既是深度阅读,也是他最初写作的引子。写作是锤炼母语的实践,自然也反哺了翻译工作。翻译与写作成为双重奏,奏响了余泽民的文学之路。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对余泽民来说,大量的翻译工作仍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家中完成,他住在一个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中,装修简单,他并没有“书房”,甚至没有固定的书桌,经常是靠在床头,电脑放在腿上完成翻译工作。“我一开始翻译就可以连续十个小时,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态。”
看书,打字,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自嘲“是在匈牙利最穷的中国人”。“2004年我才有了自己的这个小房子。由于家里很乱,有时候我会去咖啡馆工作,或申请去巴拉顿湖边的‘匈牙利翻译之家’,那里离布达佩斯一百多公里,是一栋漂亮的小别墅,也是文学翻译的小联合国。在那里不仅可以闭关工作,还会有一些食宿补贴。”
2017年,余泽民获得了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奖励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机构”。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在将优秀的匈牙利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越来越多的匈牙利作家、诗人都将余泽民视为“走进中国的一扇门”。
“我感到很高兴趣策略,自己做的工作在匈牙利当地的文学圈中被承认、被尊重,这也是我翻译的价值所在。”与此同时,余泽民也深刻感受到沉重的责任,“当别人把所有当代匈牙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都放到我身上时,我能做的,就是花更多精力与时间,不断去翻译优秀的作品。同时,我也会将中国的作品带到匈牙利。”
近十年,在余泽民以及众多中匈文化摆渡人的努力之下,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文城》、苏童的《米》、邱华栋的《时间的囚徒》、鲁敏的《此情无法投递》、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田耳的《被猜死的人》以及艾青、吉狄马加、梅尔、杨炼等名家名作与当地读者见面,他们还让中国年画、汉画像石、戏曲故事等文化书籍摆上了匈牙利人的书架。
如今,余泽民作为特聘教授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匈牙利国情和匈牙利文学阅读与翻译课程,每年定期在国内小住,还会在北外、中传和其他大学办讲座,接触到了大量中国年轻人,在丰富的履历里又添了一个内容。他谈道:“翻译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之上的,同时又要不断精进母语。我们看到的翻译作品,也就是这些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工作是在幕后。文学翻译是很苦的一行,对此必须要有热爱才能不断前行。”
采访接近尾声,天色已从晌午转至黄昏,余泽民即将赴约下一个行程。他背起一个黑色的书包,简单挥手告别,用他对文学的热爱与毫不掩饰的真挚继续铺筑更多文化交流的道路。
Q-北京青年周刊
A-余泽民
条条大路通文学
Q 你的母亲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所以,你最初学医是不是受母亲的影响?
A 对,那是原因之一,我妈妈的确是一位特别好的妇产科医生。我记得,小时候经常有人给她送感谢信,送锦旗,所以她是我的榜样。还有一个原因,高中我上的是理科班,但我不太喜欢学数理化,高考报名时,我把医学想象得很简单,以为记药名、做手术就可以当医生,没想到进了北医,不仅要学内外妇儿,还要学药化、生化、物化和电工原理。
Q 硕士期间转而就读了艺术心理系?
A 是的,我在本科期间就很喜欢看文学和社科书,看到名著就要买,阅读量在我周围的朋友中算是很大的。当时,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而且,那时候弗洛伊德刚刚传入中国,是特别火的。教育改革,北医改革出了一个“小学期”,每位同学可以选一个感兴趣的科室做三个月的科研课题。我选择了“精神卫生研究所”,也就是精神病院。那些病人的简历就像一部部小说,很吸引我,让我感觉人性的复杂。我先后参与了两个很先锋的课题,一个是李从培教授的司法精神病学,一个是方明昭教授的性变态行为治疗。毕业前夕,我听说中国音乐学院有一个新学科——艺术心理学招硕士研究生,于是我就考了去。不过现在回想,无论我学医、学艺术、学心理学,还是后来出国进入了社会大学,所有学习的都是“人学”,冥冥中都将我朝文学的路上指引。我能够走到今天,走到这里,都因为我对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在我看来,条条大路通文学,不是吗?
Q 后来孤身去往匈牙利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呢?
A 原因很简单,就想去看看世界,听说匈牙利当时不需要签证,买张火车票就去了。所以,那会儿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可以出国的机会,而且没有门槛,正好满足了我想看更广阔的世界的念头。其实,如果这个念头再停留几年,我没有行动的话,可能就会前思后虑了。因为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是很莽撞的,但也是因为这样的莽撞,最终把我指引到了这样一条路上。所以,我有时候总跟学生说,青春就是我们可以挥霍、用来奋斗的本钱,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做一点“荒唐事”,不知道命运会给你引到何方。当然这种“荒唐”是需要有内心原动力驱使的。
Q 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作品与大家见面?
A 我翻译的拉斯洛新书《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刚刚印出来,它可以被视为《撒旦探戈》的续篇,踩中了诺奖的鼓点。明年,我翻译的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的代表作《和谐的天堂》将由译林推出,本来他也是诺奖热门候选人,可惜患胰腺癌去世了。另外,我还翻译了匈牙利大作家纳道什·彼特(Nadas Peter)的《平行故事》三部曲,期待能够与读者见面,他也连年都在诺奖的猜奖名单里。接下来我要翻译的也是拉斯洛的两本小说。另外,还开始写一部我与匈牙利文学的回忆之书。
文 王雅静
编辑 韩哈哈
人物摄影 解飞
场地鸣谢 北京展览馆 COFFEE G
陈思亮:自在的韵律
史依弘 与京剧的百年对谈
李娜 刚柔并济 逐冠人生
潘展乐:赛场上没有退路 只有拼到底
张雨霏 蝶变之后
王羽佳:探索不止 恒动不息
汪顺:年龄只是数字 实力说明一切
新 刊
「 2025年11月13日 余泽民 」趣策略
星速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